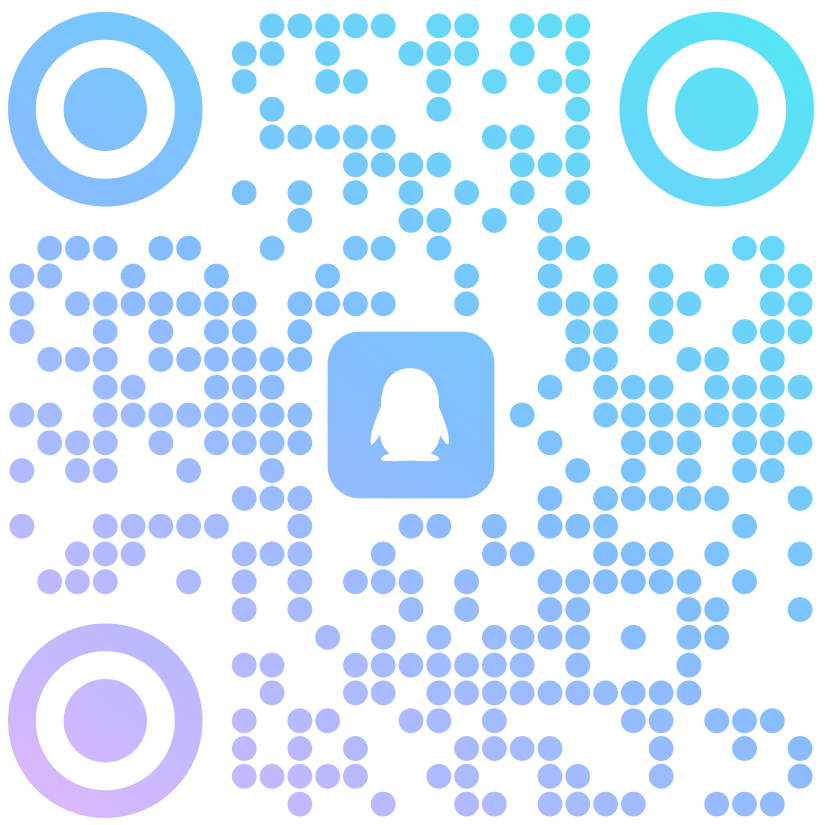群山和人群

团建刚结束,生活又迅速被北京的节奏拉紧,几天前的松弛反而在此刻清晰起来。于是拿起笔——我怕再不写点什么,这种记忆的余温就要像水汽一样散了。
按理说,“团建”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点社交义务的味道,但相似的境遇,让几个同龄人的初次见面也能熟络得像一起翘课的同班同学。也对,成年人的距离感多半不是来自陌生,而是心里的戒备和疲乏。若彼此都愿意喘口气,倒也能轻松靠近。
抵达大理的时候是个阴雨天,浓雾把苍山吞没,洱海像张被揉皱的白纸,到处灰蒙蒙的。好在隔日天公作美,一早便云朗天清。站在玉带云游路上俯瞰洱海,山和海都被淘洗得明彻而透亮。昨日什么都看不见,今天却豁然开朗,有些风景注定要靠一点运气。
我对那些为拍照而建的白墙打卡地实在兴致寥寥,好在崇圣寺的千年古刹能让人真正静下来。殿堂深处的佛像金身巨大,抬头仰望时,思绪仿佛也被引到了某个更高远的地方,凡尘喧嚣也显得渺小。可惜行程紧,停久了便会被催促,成年人的旅行自由,甚至不包含步伐的速度。
晚上在古镇里玩狼人杀,这家小店的主人很年轻,见缺一人便爽快入局,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自在,是我羡慕的状态。工作后少有这种情绪外放的时刻,可以放肆争吵、辩解、拍桌大笑。折腾到半夜,一行人跑到龙龛码头,看了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日出。
那一刻,脑海里闪回两年前和朋友们爬山迎日出的夜晚——热闹总是相似的,可同行的人早就换了一批。
旅程将尽,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安稳。不是因为谁在等我,也不是要去哪儿报到,而是我终于觉察到:哪怕身边的位置一个接一个地空下来,我依然能看到新的风景,依然能讲出新的故事。
想起返程那晚的航班,窗外,天光偶尔照亮群山,而人在城市的阴影里继续走路——光亮与自由都不常在,但偶尔一次,就足以继续往前。